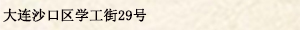寓言中的儿童文学属性思考
作为思想源泉的寓言,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寓言的古老与常青,来自于智慧的高度,而不只是文体的新颖。如果不把寓言放在人类思想和智慧的高度来认识,只是作为一种文体形式来对待,那将是当下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滑坡与呆小病,让古老的智慧情何以堪。如果中国儿童文学无视民间文化传统,只把自己定位于近现代文化的产物,只是从西方文明之中嫁接出来的一种教育儿童的工具,那就是对自己文化源头的自卑感在作怪。中国先秦以及诸子百家的许多寓言,多是中国古老智慧与文明的化身。中国古代寓言和西方经典寓言应该是全人类的财富,把这些财富进行现代转化,变成对当下儿童生命成长的良师益友,才是正途。我们不能够拿西方类寓言的流行文化和畅销书作为发展方向和创作目标,那是走向死胡同,精神内涵容量只能越来越窄。技术至上,比如说一个华丽的故事、一段不俗的语言、一段浅薄的道理,并不是寓言的发展方向,更不是儿童文学的未来。当下中国寓言创作的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寓言传统丢失了,开始向儿童文学中的庸俗化与市场化趋势发展,以冗长的故事、媚俗的娱乐、虚假的道理、心机的复杂、利益的得失、耍小聪明等作为创作方向。这是一种自我沉沦的表现,发展下去令人担忧。如果把《谁动了我的奶酪?》那样的畅销书,定为中国寓言的发展目标,以销售至上的广告策略、虚张声势的心理恐吓为目标,则降低了寓言的品质,势必造成寓言写作的低级与浅薄,削足适履,给自己穿小鞋——水晶鞋,看上去很美。从《庄子》开始,寓言就是对“道”的寻寻觅觅,作为形而上之道,无形无象,无所在又无一处不在,颇有老子《道德经》强调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即西方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从形而下来的角度看,寓言又是一种生存智慧和养生法则,《庄子》的“养生主”有形有象,有人有事,充满了人事的繁华和乐趣,甚至就是一种美的生活方式,连《庖丁解牛》都充满了美的享受和质感,充溢着对日常生活的美学态度和诗性希望。从实质上看,寓言不是针刺,更不是给人治病,而是治人,更是养生,在于遵从天道、敬畏自然、以柔克刚、守弱处下、上善若水、利于万物而不争的“水”的性质。如果说寓言是儿童文学,或仅仅归入儿童文学,则更是贬低了寓言,寓言是超越儿童文学并包容儿童文学中具有智慧和哲理因素的部分,这一部分的儿童文学又是儿童文学精华中的精华。如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对人类社会虚伪的揭批,何等犀利与深邃;安徒生《豌豆上的公主》,对人性矫揉造作的反讽,何等温婉而含蓄;安徒生《枞树》,对人生刹那辉煌与久远安生的比对,何等诗意而尖锐;安徒生《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思考人生的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何等幽默与风趣。哪一篇童话不是最好的寓言?那是关于人类智慧和真理的探索,用象征与隐喻的笔法,并不直接告诉读者一个什么大道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人进入这些故事,都能获得一定的积极生命体验,因故事里的“奇人奇事”与自己无关,与自己的生活无关,在阅读时便获得一种审美距离和“间性”,在会意一笑之后,却是无尽的沉思默想,向着人类的智慧,也向着人类的愚昧,再一次出发。动物们,住在童话家里和住在寓言家里动物在寓言和童话里都是绝对的主角,但是,这些主角在不同的“家”里功能不完全相同。站在寓言的家里看童话和站在童话家里看寓言,是完全不同的。寓言和童话的家里,摆设的家具都有桌椅板凳等,寓言家里的摆设是用来治病救人的,童话家里的摆设是用来游乐人生的。寓言无显性逻辑,但有强大的隐性逻辑,天鹅、梭子鱼和虾一辈子都不可能一起遇到一辆小车,寓言故事却可以让他们相遇。童话的显性逻辑十分重要,狐狸如果要打猎人,一定要有充分必要条件,条件成熟,才可以打猎人,才可以一同游戏。人类的愿望和情感旨归为童话的隐性逻辑。童话出生为情所困,寓言出生为理所扰,情与理是文学的经与纬,是人的精神和情感符号。玩理时要有趣,无趣就无味;玩情时要有理,无理便无道。仅此而已。任何对童话的殖民与对寓言的强权,都不是文学的愿景。一方面,任何一种文体的变种,都是对一种文化生态的破坏,人们要警觉文化生态被破坏;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体的变种,都是一种文化的裂变和重生,人们要努力促进新生命的诞生。相同的瓶子装着不同的料。类似寓言的童话和类似童话的寓言,都属于次生文体,可以存在,但无法以此来确认另一个文体种类。在克雷洛夫的寓言《天鹅、梭子鱼和虾》中,什么让天鹅、梭子鱼与虾相遇?一辆陷入泥淖里的小车——这是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的社会洞悉、高度的智慧凝结。在金近的童话《狐狸打猎人》中,什么让狐狸打猎人?对弱者的同情,对规则的反驳,对现实的推翻,对一种新现实的寻找和呼唤,对人类自我中心的嘲讽,也可称之为对思想的具象化与完成。最终,这篇童话借由狐狸,显示人类的智慧。借用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语言方式:“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在谈论寓言和儿童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自我超越的焦虑,我们在谈论如何呼唤经典作品问世,我们在谈论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如何完成,我们在谈论受新媒介和文化传播环境的影响而不惊慌失措,我们在谈论受读者期待的摆布而坐怀不乱,我们在谈论……我们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乌鸦喝水的困境,思之难,美之难,退亦难,进亦难。无论是童话,还是寓言。当人类以动物的形象作为瓶子,承载人类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时候,动物却不以为然。大鹏鸟还是大鹏鸟,燕雀还是燕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啊?!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寓言与儿童文学具有相同的梦想儿童文学作家把自己对世界的价值取向、审美立场和叙事方式表达在文本中,通过文本与读者形成对话,如果这样的对话是真诚的、平等的、友好的、有启发性的、有意义的甚至是有趣味的,我们就把这样的叙事称为伦理叙事。反之,成人作家如果通过文本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意识,叙事时使用教训的、挖苦的、讽刺的、打击的霸权话语,我们就称之为非伦理叙事。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很好地进行伦理叙事,把作家自我的心灵感受通过平等的方式传递给读者,既不高高在上,又不故意蹲下来装腔作势。当儿童文学作家能够真正地看到寓言之中的儿童文学属性,就可以与寓言进行友好合作,并互利互赢,互通有无。当寓言不只是一种思想或者理念的载体,而作为一种文体,尤其是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时,往往会从多个方面展开全新的精神内容和艺术形态,也就是寓言中的儿童文学属性表现最为突出的几个面相。第一,强烈的情感性。作品如果没有情感,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文学艺术。爱的母题是儿童文学的永恒的艺术追求。在情感的表达上,希腊的《伊索寓言》、印度的《百喻经》和中国的先秦诸子寓言,大多数以严肃说理为主要风格。但是,进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寓言以达·芬奇为代表,不再以宗教的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展现人的七情六欲以及丰富的情感世界。他的寓言《金翅雀》便是时代和社会生活人类思想的象征,“不自由,毋宁死”成为当时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当金翅雀爸爸那种失去孩子的痛苦、寻找孩子的艰辛、见到孩子的欢愉、放弃孩子的决绝等复杂的情感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父爱如一条奔腾的河流,撞击着读者的心。这篇《金翅雀》毫无疑问被会纳入儿童文学的范畴,因其带有鲜明的儿童文学属性。在《金翅雀》中,儿童文学与寓言做了很好的融合,成为一种艺术经典。“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给人以快感,又给人以一种严肃的、思想的满足。”[1]文学的情感逻辑,有时候超越了现实的理性的逻辑,又在这种情感的超越之中形成了更深刻的思想性,也就是艺术境界的提升。《金丝雀》中情感的浓烈以及父爱的残酷有别于平时的父爱,是日常生活之中“父爱的社会性”的一种具体形象艺术的升华。在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的《论儿童文学三大母题》中,“爱的母题”之下区分了父爱型儿童文学与母爱型儿童文学。父爱型儿童文学具有社会性,把儿童带入社会环境之中,以适应生活的残酷的一面,针对的读者对象是那些稍微成熟一点的大孩子;母爱型儿童文学更具有自然性,以母亲的无私奉献和保护儿童为主,针对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小一点的孩子,这一类儿童文学作品给孩子爱和温暖。《金翅雀》这一篇寓言无疑是一种父爱型的儿童文学,撞击儿童的心灵世界,不只是在社会的“囚笼”之中认识自我,还要看到“金翅雀父亲”一类人面对“囚笼”困境的解决办法。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的一种表征,与进入了21世纪的人的价值观念还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丰富的幻想性。这是寓言的精华,也是儿童文学创作思想深刻的一个源头活水。我们反观古希腊时期的《伊索寓言》之中的一些故事,无论是《狐狸和葡萄》《龟兔赛跑》《狼和小羊》,还是《狼来了》《农夫和蛇》《愚蠢的驴子》,基本上都是观念先行之作,这些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德至上的成人价值观,以及成人社会的功利主义计算与得失,与儿童的心理和情感难以产生共鸣。这种故事原封不动地拿来,其目的性突出,讽刺性和劝谏性也让儿童很难获得认同感。但是,这种类型的寓言故事想象力极为丰富,可以成为一个现代人创作新故事的一个潜在文本,如一个树根一样,新的故事可以从这些原型故事之中生长出来。比如美国绘本作家李欧·李奥尼的图画故事书能够被儿童和大人同时接受和喜欢,大人可能接受里面的哲思,孩子可能喜欢故事的趣味和想象,他的图画书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寓言性,带有深刻的人生经验。比如他的代表作《田鼠阿福》,写了一个叫阿福的小田鼠,在秋天大家都在收集粮食采集果子准备过冬的时候,他却开始对着秋日采集阳光和秋色,而不去劳作。到了冬天,田鼠们躲在地洞里,感觉暗无天日,食物缺少,寒凉寂寞,无聊至极,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田鼠阿福让洞里的小老鼠闭上眼睛,当他说到金色阳光,老鼠们就感觉到温暖了,而当他说到蓝色的长春花、红色的罂粟花和草莓丛中的绿叶子,老鼠们已经感觉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些画一般的颜色。田鼠阿福为他们朗诵自己作的诗歌,他们的生活也不再枯燥寂寞与难耐。这充满生命体验的图画故事,带有《伊索寓言》之中《蝉与蚂蚁》故事的影子,只不过寓言里面歌颂了蚂蚁的勤劳,讽刺蝉的懒惰。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思想蕴藉完全不同。可以说,古老的寓言就像老祖母一样,给孩子带来无限的慈爱温暖、快乐与幸福。第三,益智的游戏性。除了上述儿童文学作家把古老的寓言的价值观进行转换,变成拥有现代儿童本位观的儿童文学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儿童文学借助寓言故事本身的人物情节和故事结构,形成新的故事。这也是孩子很喜欢的一种创作形式,让他们参与到寓言故事之中,与古老的寓言进行游戏,续写或是改写寓言故事。这里没有了故事的教训意义,也就是基本上摒弃了寓言故事后面的说理,只是形成一种思维的游戏,孩子在游戏之中增长快乐和智慧。比如说敖幼祥的漫画《龟兔赛跑——现场推论》,在原有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故事的基础之上,变换了乌龟和兔子每一次赛跑时候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以及故事主人公个人的状况。比如说兔子感冒了生病了,或许就没有办法赛跑了;或许在比赛的终点,撞线的时候,拉线的人是乌龟的亲戚,兔子跑到了终点没有人拉线,乌龟到了就有人拉线;或者不是兔子睡着了,而是乌龟找到了另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乌龟等在终点,兔子必然失败……还有许多其他各种各样情况的变化,这种构思的多元化、多角度、开放性,不只是让老故事发新芽,更在于幻想的无限可能以及“思考本身的乐趣”。而思考恰好是人最宝贵的能力。古老的寓言让儿童文学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凌空翱翔,或者说现代儿童文学创作让古老的寓言故事迎面碰上了当代人的童年,开始无忧无虑地与作者游戏。正像荷兰文化史学者J.胡伊青加在《人:游戏者》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能称为真正的人”,“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儿童,正是人类游戏的主体,他们的思维带有鲜明的游戏性,如果不给他们自由舒展的游戏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他们很难实现自我。寓言被用作游戏的目标和主体,并在不断消解寓言的规定性价值的同时,创造新的寓言,在新的寓言诞生的时候,古老寓言不但没有消逝,其原始价值——思想性、艺术性等——还会在这种不断地被“解构”的过程中,得到最有效的传播。也可以换一种说法,这是寓言“无为而治”过程之中,最了不起的“治”了。一如汉字的笔画、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五线谱等等,都起到了文化的原点作用。第四,形象的鲜明性与画面的生动性相得益彰。在以往对寓言的阅读之中,人们经常会沉浸在故事的神奇与说理的透彻上,很少置身事外,把故事与自我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这些经典的寓言故事。从审美心理学上说,距离产生美。那些经典寓言故事能够流传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故事的画面感极强。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如《螳臂当车》《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鹬蚌相争》《盲人摸象》等等,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和一幅幅妙趣横生的画面就在读者眼前,如放电影一样一幅幅地展开。《螳螂捕蝉》这样的故事,是一种物理世界各种事物关系的生动表达,又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智慧与生命哲学,更是一种“看”与“被看”的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在这种关系视角的转换之中,艺术张力形成了,完成了艺术创造和对深刻意义的领悟。亦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美国艺术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一件事物是独立存在或单独存在的。看到一件物,就意味着给这件事物在整体中分配一个位置,它在空间的位置,它在那些用来度量大小、亮度、距离的仪器的刻度盘上的位置等等。换句话说,每一次观看活动就是一次‘视觉判断’。判断有时候被人们误以为是只有理智才有的活动,然而‘视觉判断’却完全不是如此,这种判断并不是在眼睛观看完毕之后由理智力做出来的,它是与‘观看’同时发生的,而且是观看活动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在中外经典的儿童文学中,形象鲜明的长鼻子匹诺曹、长袜子皮皮、小熊维尼、小猪唏哩呼噜等都是人物画廊里的主人公,也被孩子们喜闻乐见。故事能否给读者以画面感,是衡量儿童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如《童话小蝌蚪找妈妈》之中,小蝌蚪黑黑的大大的头、短短的尾巴,在水中游着,扁扁嘴的鸭子、两只大眼睛大鱼、四条腿的大乌龟、白肚皮的大白鹅、穿着绿衣服的大青蛙等等,都有鲜明的“形”与“色”,动感十足,给人活灵活现的感觉。总之,世界经典的寓言如天空一样浩瀚无垠、博大精深,其中既有脚踩大地背负重担的驴子,又有遨游宇宙天际的大鹏鸟。这些古老而神奇的生命智慧和思想资源,只有常读常新,不断地被日常生活所使用,与人类有肌肤之亲,才能发挥其隐形衣的作用,同时,又不仅仅是隐身衣,还是人类梦想的彩衣——如果说人类梦想拥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童年的方向。注释:[1]阿诺德·豪塞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选自《中国寓言研究》第二辑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